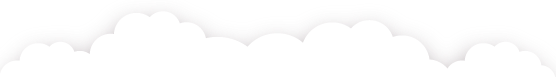《我的五行传承之路》一书是诺娜·弗兰格林(Nora Franglen)老师对自己几十年践行五行针灸的回顾。本书由杨露晨翻译,中文版即将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经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授权,在本书正式出版前,其内容将在五行针灸学会微信公众号陆续推出。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刘观涛老师读后感言:此书无论著者还是译者,都将一个绚丽的精神世界展现给我们,读之,进入了《浮士德》里面的一句经典台词:真美呀,请停留一下!
教五行针灸(上)
我注意到我的教学方式开始呈现出另一种形态。我发现,无论是英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现在范围更广的中国,都要求我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而不是照搬之前当学生时学到的模式。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教学经历对我的帮助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让我惊讶的是,虽然他们接受的五行针灸培训只是西方同行的一小部分,每年能从我们这里听到的课程也只有短短几周的时间,他们学起五行针灸来却正如俗语所说,“如鱼得水”。
我意识到,这种对全新针法的开放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与数千年的文化传承有关,至今,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仍依托于这一传承。把五行针灸重新引入这种文化,好比在为他们打开一扇能看到熟悉风景的大门。西方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学生们需要去预先熟悉这些全新的理念。
考虑到这种文化传承的差异,便需要想出不同的教授五行针灸的方法。因学生所在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所需要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视学生对传统针灸核心哲学概念的熟悉程度而定。
无论是我成长于其中的西方模式,还是后来我创办并任教的五行针灸学校(SOFEA),都是基于三年制大学式课程这一传统结构。
然而,这种模式并非普遍适用,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如此。很明显,三年的课程所能覆盖的范围与一年只持续几周的课程截然不同。
但令我惊讶的是,尽管五行针灸与他们之前所学的现代中医的原理如此不同,中国的学生却能很快在临床上做出调整,使之与五行针灸的要求相契合。于是,这让我反过来开始更加仔细地思考英国针灸学院标准的三年制课程背后是基于怎样的假设。
我刚开始创办五行针灸学校(SOFEA)时,完全照搬了在华思礼教授的莱明顿学院学到的模式。
第一年,我们会学习所有中国文化的哲学原理及其在传统医学中的应用,还会学习与穴位定位相关的解剖学知识。
我们会花大量的时间学习五行和十二官,老师还教导我们深入大自然去观察五行,因为四季的韵律正是五行的造化使然。
我们还会开始观察五行在我们自己及遇到的每个人身上是如何运作的。
到了第二年,我们开始将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为一些志愿者病人诊断五行。到了这一阶段,我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做着一件可以被视为自身使命的事情。
整个第一学年,我都仿佛在梦游,只把学校的时光看成是我原本就很充实的生活的有趣点缀。我之所以决定学习针灸,是因为很想了解这门对我影响如此深远的学科,却并没有成为针灸师的打算。在针灸教育的早期,这是完全可行的,因为相比现在的学费,那时的费用要低得多,而且当时的课程安排比较分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月才上一个周末的课),可以很容易做到不影响工作。
当时,即使是没有受过太多正式教育的人申请学习,学校也是鼓励的,不像现在,申请者都需要通过A-level考试(译者注:A-level是英国全民课程体系,是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高级水平课程,也是英国学生的大学入学考试课程。A-Level课程证书被几乎所有英语授课的大学作为招收新生的入学标准),因为当时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慈悲心,而不是学习书本知识的能力。
实际上,华思礼教授是不提倡死读书的,他常教导我们要放下书本,向大自然学习。我们要成为“大自然的工具”,同时,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标准要求自己的。
最后的第三年几乎完全是临床,期间我们必须治疗一定数量的病人,还要观察其他同学的治疗。
由于病人需要频繁的治疗,于是上课的时间变成每周一次。每周六一大早,我都会从伦敦出发,在高速公路上飞驰两个小时去往学校,车上还经常会带一位伦敦的病人。
我们只有完成了规定的临床治疗时间后才能毕业,同时还需要得到老师的认可,认为我们有能力处理病人摆在我们面前的许多情感问题。
因此,在我接受培训的过程中,我们三年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集中在学习如何找到每个所遇之人的五行上,其中,老师还鼓励我们多看电视,这也是提高诊断技巧的方法之一。
三年下来,我们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可达数百个小时。相比之下,我现在能提供给中国学生的时间少之又少,但这是他们以及任何想进入到五行针灸这一领域的中医师必须接受的。
因此,能有三年的课程时间潜心钻研五行,我们何其幸运,这也是让中国治疗师异常羡慕的地方。
他们所拥有的只有每年为期几周的研讨会,不过,他们也可以继续投入热情,采取自学或小组学习的方式对我们所教的知识进行补充。由于老师实在太少,除了鼓励他们转换心态,将自己视为先驱者外,别无他法。
因此,如果有人想学习五行针灸这类学科,需要向华思礼教授以及曾经与他一起追寻针灸真理的那群同伴学习,他们当年也只有很少的学习机会,大部分时间都靠自学。
其余的时间里,当他们各自回到英国的不同城市时,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所学的知识发展出自己的特色,虽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均以传统理论为基础。
华思礼教授在他的家乡莱明顿(Leamington Spa)创建了一所学院,玛丽·奥斯丁(Mary Austin)则在伦敦中心区建立了另外一所,迪克·冯布仑(Dick van Buren)则创建了国际东方医学院(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Oriental Medicine, ICOM),现在仍然是苏塞克斯郡(Sussex)的东格林斯特德镇(East Grinstead)的一所教学学院。